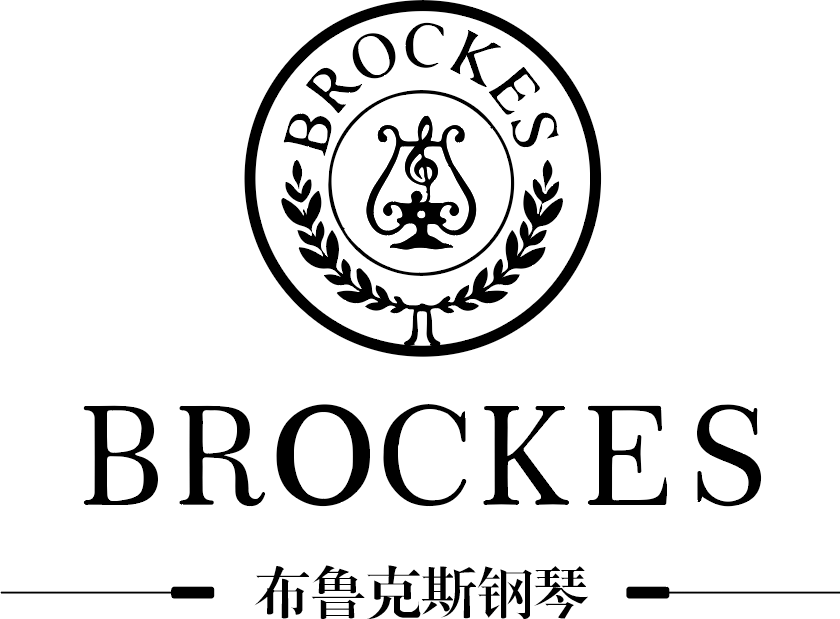
钢琴学习心境尤为重要
来源:
|
作者:pmtf6cc5f
|
发布时间: 2020-06-16
|
802 次浏览
|
分享到:
只要是学习,任何学科都有一个“程度”问题,学钢琴也不例外。我们的《业余钢琴考级》自一级至十级(或九级)就是按“程度”由浅入深循序而渐进,与学校的年级是一个概念。不同之处在于,钢琴的级别不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学龄决定,而是由考生自己或老师、家长选择的。这就必然存在一个如何对待程度的认识问题。让程度联系实际非常重要,否则脱离实际水平只讲级别,谁不愿意越高越好?
程度是什么?这个词只是在教学中用到,其本身与艺术水平可谓毫无关系。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当你有能力弹莫扎特的奏鸣曲时,你弹不了肖邦的奏鸣曲,是因为两曲的程度相差太大;但当一位成熟的钢琴家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时,你能说他的程度太浅,不如我们能演奏肖邦奏鸣曲的普通学生吗?为什么一个天才的钢琴家会数十次地练习一个连十岁小孩都不屑一顾的音乐片段?
程度只是我们学习钢琴的阶梯,要一步一步地走才行。程度的高低与水平的高低完全是两回事。
记得曾有一件令我哭笑不得的往事:某个城市邀请我去开独奏音乐会,当我将节目表发过去后,对方便断然收回了邀请。原因是我曲目中有一首《牧童短笛》。主管领导认为我的水平不够,因为这首曲子她的小女儿一年前就弹过了。我无言以对,如果我说《牧童短笛》对你的女儿可能很容易,而对我却很难的话,他可能相信吗?会不会进而怀疑我是江湖骗子?无奈只得取消了演出。
郎朗演奏《牧童短笛》
有一位母亲带着她11岁的女儿来找我,准备参加业余十级的考试。听完她女儿的弹奏后,我直言:“你女儿还不具备弹奏十级曲目的能力,有太多的问题是无法在这些曲子中解决的,可能选择五级的曲目对她的进步更为有益。如果勉强参加,也不可能通过。”她一脸难色地对我说:“您说得不错,孩子的确非常吃力,为了弹好这几个曲子已经练了一年多了。学校的功课很重,所以我们希望她能早日通过十级……”我茫然了:难道如此辛苦的目的,就是为了拿个一文不值的证书,然后把钢琴丢掉?
程度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是个人实际水平的标尺,每一级都有各自的标准,必须循序渐进。试想一个小学各科不及格的学生,如何能接受中学的课程?更何况像刚才提到的那位11岁的小姑娘,简直是准备上大学了!

因为对程度的误解,许多人以为只要把某高级别的曲目弹下来,就算达到了该程度,于是大力发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愚公移山精神,将力所不及的曲目生啃硬背下,大有不弹下来誓不罢休之势。然而其害无穷!成语“揠苗助长”比喻得实在贴切,苗因其根断而死亡,我们的钢琴学业也会因其“根断”引起的营养缺失而断送。揠苗助长的后果除了能炫耀一下我(或我的孩子)是几级之外,不仅一无所获,还会走入歧途、断送前程。
在一次公开课上,一位被主办方推荐上台的小男生为我演奏了一首选自十级教材的奏鸣曲。由于作品的程度远远高于他的实际程度,我的任何指导对他都勉为其难。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他的确是一个很聪明、有悟性的孩子,便在课堂上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到课间休息时,我故意避开他满面兴奋而自豪的家长,请他拿着乐谱到了一个僻静角落,打算告诉他一些演奏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我看到在他的谱面上密密麻麻写的汉字竟然比音符还多!在最显眼的右上角更有赫然的五个大字:“蚂蚁啃骨头!”在讲了几个具体问题之后,我问他:“你觉得这首奏鸣曲好听吗?”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他:“你喜欢弹钢琴吗?”他脸顿时红了,更为轻微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你十级都过了,今后还继续学吗?”这次他摇头的动作又快又坚决。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心中顿生惆怅:有多少这样的孩子,为了追求“高程度”,含泪挣扎在黑白键上,常年如“蚂蚁啃骨头”般地死啃几个考级曲目,却因不堪重负而失去了对音乐的感知和兴趣啊
选老柴还是贝多芬?
应该说,把握程度的关键在于教师。作为单独授课的钢琴老师,第一,要认真观察和研究每一个学生的实际程度,有计划地布置作业。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选择既有相对难度又有可能收效的曲子。使学生能够通过练习切身感觉到自身的进步,感觉到越练曲子越好听,感觉到越练钢琴越好听。第二,不可听任家长在教材上提出任何不切实际的要求,要耐心向他们解释钢琴教学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申明利害。至于极个别利令智昏、甘愿拔苗致死的家长,一定要拒绝授课,不做好好先生。
做一名优秀的教师有很多要研究的学问(这里仅就程度问题而言),要懂因材施教,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这些比教师自己的演奏水平重要得多。
我就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毕业考试曲目需要有一首大型的钢琴协奏曲。我的老师李昌荪教授曾犹豫在两首曲目之间: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与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当我打探到这个计划时,心里着实期盼老师选择前者。除了我喜欢这个作品之外,主要原因是大家公认老柴第一的程度比贝多芬高得多,况且在当时的附中还没有人弹过呢。不料李先生最后选择的是贝多芬第四,令我大失所望。事后我问他,当时为什么如此选择?他说:“我认为贝多芬第四对你的音乐理解和手指功夫都更有好处。你把贝多芬弹好了,再弹柴科夫斯基会很容易,可弹好了柴科夫斯基却未必能弹好贝多芬呀!”
齐默尔曼与伯恩斯坦合作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

二十多年后我随中央乐团赴香港演出,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得到了热烈欢迎和极高的评价。我默默地对着李先生的在天之灵说:“虽然这部协奏曲是我工作后自己独自完成的,可其中的一切都源于您当年的教导。”
我经历的“压”与“拔”
对一个优秀教师而言,把握程度也并非易事。钢琴教学自有本身的特殊性,必须采用个别授课的形式,无法上大课,无法统一年级和教材。学生年龄不同、起步时间不同、性别不同、天资不同、性格不同、体格不同、身体发育不同、课余练琴时间不同,再加上每个人在发展进程中都会有波浪型出现,这就要求教师在循序渐进的规律性中加上因人而异和因时而异的灵活性,在程度上根据具体情况,该压时无情地压,该拔时大胆地拔。
我至今清楚记得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第一学期,当看到公布了每个同学的期末考试曲目时,当场就哭了。我在入学前已经学了四年多的钢琴,论程度在班上已居中上等。可布置给我的考试曲目竟然是朱仁玉的《五首小曲》!这是一首学生习作,每段八小节,各具标题,程度相当拜厄的前期,我们班小提琴专业的同学初学钢琴正在练呢,我能不哭吗?于是斗胆去找学科主任发牢骚,得到的只有一句话:“你认为简单,但你能弹好吗?”果不其然,一上课就傻眼了,那么多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上课,可总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但有一点,就是切身悟到了:弹好钢琴真不容易。今天想来,如果那时不压我的程度,能领会到这个真谛吗?
在附中的前三年里我的程度在班里一直居中,折合成当今《业余考级》教材相当于六至七级吧。突然,老师让我弹李斯特的《第十二狂想曲》,可把我吓坏了。当时顾圣婴在音乐会上演奏此曲,把我们钢琴专业的同学都震撼了。动听的音乐加上她的辉煌技巧,使我们觉得这完全是一首可望而不可及的高难作品。大概因为年轻,挑战激发了动力,我不仅弹下来了,还多次被院里拿出来展示(那时称作“招待外宾”),可见还算弹得不错。
范·克莱本演奏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NO.12
如今回忆这两个亲身经历,可算够典型的了。一个压得够狠,一个拔得够凶。只有在自己成为老师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对程度的“压”与“拔”,是教学中的重要手段。适时、适度地运用程度来促进教学非常重要,关键是看教师会不会把握。当一个学生连“弹好”的概念都没有时,一定不能图进度。而当一个学生已经具备了正确的演奏概念和技术能力的储备,一定不能墨守成规,要敢于发掘他的潜能。至于何为适时、何为适度,则是对教师水平与经验的考验,其中大有学问。
比赛中的程度
我担任过非常多的比赛评委,经常会遇到有些选手因为选择的曲目过难,演奏时的负担颇重,使质量大打折扣而落选。我猜想,这些人(或许包括他们的家长或老师)大概是以为弹程度高的曲子评委会给加分,弹程度低的曲子评委会打低分吧?非也。
其实评委在评比的过程中从来都是看你弹得好不好,而不是看你弹的难不难,程度只是在制定比赛曲目范围时(往往根据年龄)做出的设定。在一次青少年钢琴比赛上,内地院校的选手几乎都选择了李斯特的高难度作品,结果全军覆没。最后奖项几乎全归于“香港军团”,他们选择的作品可以说是程度低多了(如《舒伯特降B大调即兴曲》),但质量很高,得了奖。评委吃饭时,阿里·瓦迪(Arie Vardi)问我:“为什么他们要选那么难的李斯特作品?”我知他是明知故问,且一言难尽,只得摇头一笑。我们内地的选手似乎生怕被埋没,选的曲目一个比一个难,弹得一个比一个快和响,可声音却一个比一个难听。你想展现你的程度,可我们却在关注你的音乐表现;你想展现你的“武功”,我们却在关注你的声音技巧,完全没对上茬儿。
程度是什么?这个词只是在教学中用到,其本身与艺术水平可谓毫无关系。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当你有能力弹莫扎特的奏鸣曲时,你弹不了肖邦的奏鸣曲,是因为两曲的程度相差太大;但当一位成熟的钢琴家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时,你能说他的程度太浅,不如我们能演奏肖邦奏鸣曲的普通学生吗?为什么一个天才的钢琴家会数十次地练习一个连十岁小孩都不屑一顾的音乐片段?
程度只是我们学习钢琴的阶梯,要一步一步地走才行。程度的高低与水平的高低完全是两回事。
记得曾有一件令我哭笑不得的往事:某个城市邀请我去开独奏音乐会,当我将节目表发过去后,对方便断然收回了邀请。原因是我曲目中有一首《牧童短笛》。主管领导认为我的水平不够,因为这首曲子她的小女儿一年前就弹过了。我无言以对,如果我说《牧童短笛》对你的女儿可能很容易,而对我却很难的话,他可能相信吗?会不会进而怀疑我是江湖骗子?无奈只得取消了演出。
郎朗演奏《牧童短笛》
有一位母亲带着她11岁的女儿来找我,准备参加业余十级的考试。听完她女儿的弹奏后,我直言:“你女儿还不具备弹奏十级曲目的能力,有太多的问题是无法在这些曲子中解决的,可能选择五级的曲目对她的进步更为有益。如果勉强参加,也不可能通过。”她一脸难色地对我说:“您说得不错,孩子的确非常吃力,为了弹好这几个曲子已经练了一年多了。学校的功课很重,所以我们希望她能早日通过十级……”我茫然了:难道如此辛苦的目的,就是为了拿个一文不值的证书,然后把钢琴丢掉?
程度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是个人实际水平的标尺,每一级都有各自的标准,必须循序渐进。试想一个小学各科不及格的学生,如何能接受中学的课程?更何况像刚才提到的那位11岁的小姑娘,简直是准备上大学了!

因为对程度的误解,许多人以为只要把某高级别的曲目弹下来,就算达到了该程度,于是大力发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愚公移山精神,将力所不及的曲目生啃硬背下,大有不弹下来誓不罢休之势。然而其害无穷!成语“揠苗助长”比喻得实在贴切,苗因其根断而死亡,我们的钢琴学业也会因其“根断”引起的营养缺失而断送。揠苗助长的后果除了能炫耀一下我(或我的孩子)是几级之外,不仅一无所获,还会走入歧途、断送前程。
在一次公开课上,一位被主办方推荐上台的小男生为我演奏了一首选自十级教材的奏鸣曲。由于作品的程度远远高于他的实际程度,我的任何指导对他都勉为其难。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他的确是一个很聪明、有悟性的孩子,便在课堂上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到课间休息时,我故意避开他满面兴奋而自豪的家长,请他拿着乐谱到了一个僻静角落,打算告诉他一些演奏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我看到在他的谱面上密密麻麻写的汉字竟然比音符还多!在最显眼的右上角更有赫然的五个大字:“蚂蚁啃骨头!”在讲了几个具体问题之后,我问他:“你觉得这首奏鸣曲好听吗?”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他:“你喜欢弹钢琴吗?”他脸顿时红了,更为轻微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你十级都过了,今后还继续学吗?”这次他摇头的动作又快又坚决。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心中顿生惆怅:有多少这样的孩子,为了追求“高程度”,含泪挣扎在黑白键上,常年如“蚂蚁啃骨头”般地死啃几个考级曲目,却因不堪重负而失去了对音乐的感知和兴趣啊
选老柴还是贝多芬?
应该说,把握程度的关键在于教师。作为单独授课的钢琴老师,第一,要认真观察和研究每一个学生的实际程度,有计划地布置作业。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选择既有相对难度又有可能收效的曲子。使学生能够通过练习切身感觉到自身的进步,感觉到越练曲子越好听,感觉到越练钢琴越好听。第二,不可听任家长在教材上提出任何不切实际的要求,要耐心向他们解释钢琴教学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申明利害。至于极个别利令智昏、甘愿拔苗致死的家长,一定要拒绝授课,不做好好先生。
做一名优秀的教师有很多要研究的学问(这里仅就程度问题而言),要懂因材施教,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这些比教师自己的演奏水平重要得多。
我就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毕业考试曲目需要有一首大型的钢琴协奏曲。我的老师李昌荪教授曾犹豫在两首曲目之间: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与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当我打探到这个计划时,心里着实期盼老师选择前者。除了我喜欢这个作品之外,主要原因是大家公认老柴第一的程度比贝多芬高得多,况且在当时的附中还没有人弹过呢。不料李先生最后选择的是贝多芬第四,令我大失所望。事后我问他,当时为什么如此选择?他说:“我认为贝多芬第四对你的音乐理解和手指功夫都更有好处。你把贝多芬弹好了,再弹柴科夫斯基会很容易,可弹好了柴科夫斯基却未必能弹好贝多芬呀!”
齐默尔曼与伯恩斯坦合作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

二十多年后我随中央乐团赴香港演出,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得到了热烈欢迎和极高的评价。我默默地对着李先生的在天之灵说:“虽然这部协奏曲是我工作后自己独自完成的,可其中的一切都源于您当年的教导。”
我经历的“压”与“拔”
对一个优秀教师而言,把握程度也并非易事。钢琴教学自有本身的特殊性,必须采用个别授课的形式,无法上大课,无法统一年级和教材。学生年龄不同、起步时间不同、性别不同、天资不同、性格不同、体格不同、身体发育不同、课余练琴时间不同,再加上每个人在发展进程中都会有波浪型出现,这就要求教师在循序渐进的规律性中加上因人而异和因时而异的灵活性,在程度上根据具体情况,该压时无情地压,该拔时大胆地拔。
我至今清楚记得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第一学期,当看到公布了每个同学的期末考试曲目时,当场就哭了。我在入学前已经学了四年多的钢琴,论程度在班上已居中上等。可布置给我的考试曲目竟然是朱仁玉的《五首小曲》!这是一首学生习作,每段八小节,各具标题,程度相当拜厄的前期,我们班小提琴专业的同学初学钢琴正在练呢,我能不哭吗?于是斗胆去找学科主任发牢骚,得到的只有一句话:“你认为简单,但你能弹好吗?”果不其然,一上课就傻眼了,那么多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上课,可总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但有一点,就是切身悟到了:弹好钢琴真不容易。今天想来,如果那时不压我的程度,能领会到这个真谛吗?
在附中的前三年里我的程度在班里一直居中,折合成当今《业余考级》教材相当于六至七级吧。突然,老师让我弹李斯特的《第十二狂想曲》,可把我吓坏了。当时顾圣婴在音乐会上演奏此曲,把我们钢琴专业的同学都震撼了。动听的音乐加上她的辉煌技巧,使我们觉得这完全是一首可望而不可及的高难作品。大概因为年轻,挑战激发了动力,我不仅弹下来了,还多次被院里拿出来展示(那时称作“招待外宾”),可见还算弹得不错。
范·克莱本演奏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NO.12
如今回忆这两个亲身经历,可算够典型的了。一个压得够狠,一个拔得够凶。只有在自己成为老师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对程度的“压”与“拔”,是教学中的重要手段。适时、适度地运用程度来促进教学非常重要,关键是看教师会不会把握。当一个学生连“弹好”的概念都没有时,一定不能图进度。而当一个学生已经具备了正确的演奏概念和技术能力的储备,一定不能墨守成规,要敢于发掘他的潜能。至于何为适时、何为适度,则是对教师水平与经验的考验,其中大有学问。
比赛中的程度
我担任过非常多的比赛评委,经常会遇到有些选手因为选择的曲目过难,演奏时的负担颇重,使质量大打折扣而落选。我猜想,这些人(或许包括他们的家长或老师)大概是以为弹程度高的曲子评委会给加分,弹程度低的曲子评委会打低分吧?非也。
其实评委在评比的过程中从来都是看你弹得好不好,而不是看你弹的难不难,程度只是在制定比赛曲目范围时(往往根据年龄)做出的设定。在一次青少年钢琴比赛上,内地院校的选手几乎都选择了李斯特的高难度作品,结果全军覆没。最后奖项几乎全归于“香港军团”,他们选择的作品可以说是程度低多了(如《舒伯特降B大调即兴曲》),但质量很高,得了奖。评委吃饭时,阿里·瓦迪(Arie Vardi)问我:“为什么他们要选那么难的李斯特作品?”我知他是明知故问,且一言难尽,只得摇头一笑。我们内地的选手似乎生怕被埋没,选的曲目一个比一个难,弹得一个比一个快和响,可声音却一个比一个难听。你想展现你的程度,可我们却在关注你的音乐表现;你想展现你的“武功”,我们却在关注你的声音技巧,完全没对上茬儿。
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里中骏天宸店面 13-102 TEL:18859200123 E-mail:987012328@qq.com
版权所有:布鲁克斯(厦门)乐器有限公司 备案号: 闽ICP备20009833号-3
联系我们/contact us

全国服务热线:
18859200123
(在线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8:00)
